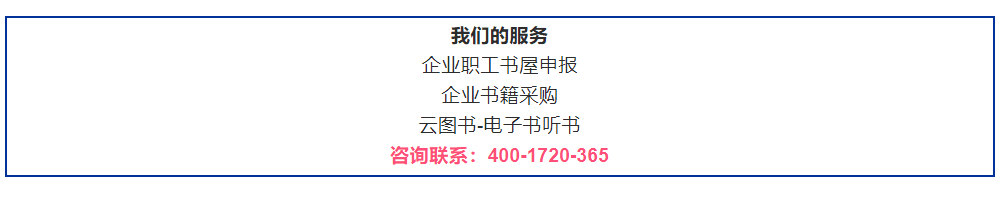四个春天
《四个春天》是陆庆屹首部文字作品,文字质朴动人,摄影温暖治愈。24篇优美散文,展现了一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、多才多艺、幽默达观的老夫妇;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、活泼生动的故乡旧人,并记述了他们诙谐且充满生活哲学的小故事;在书页间搭建起西南小城充满烟火气、人情味,同时也饱含诗意的生活景象。
张岪与木心
作者: 陈丹青“我忽然明白:要和这难弄的家伙不分离,只剩一条路,就是,持续写他……我不想限制篇幅,不愿遗漏种种细节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,给我上最后一课。”——陈丹青
张岪,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。
1982年,陈丹青、木心,先后赴美,在纽约地铁相遇,此后亦师亦友,近三十年。2011年木心去世,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,八年过去,乃有此集。书中以极尽写实的笔墨,慎重恳切的文字,送别木心,也为读者带回了木心。
罕有一个人的死亡,被如此细致地描摹;也罕有这样的文字,如此深情地凝视死亡。本书从终点出发,追忆木心一生文学与艺术的旅程。随着木心身后《文学回忆录》《木心谈木心》的出版,以及木心故居纪念馆、美术馆的先后落成,作者回顾木心在纽约开讲“世界文学史”的漫漫历程,追忆海外孤露的生活点滴、文学灵感绽放的时刻、出访英伦的旅程,更以画家的体贴与见识,缕析木心绘画的渊源与追求。再没有一个人,能这样亲切而体贴地为我们道说木心的世界。

在别人的句子里
作者: 陈以侃写出这本《一年危险阅读》的安迪·米勒,如果跟我在一个单位,恐怕会成为饭搭子。我们不但都认清,“此生非读不可的书”,恐怕八十辈子都读不完;而且,那些我们骗人家读过的书,用余生去补也早已无望了。后来他也去做了编辑,但在儿子出生后的两年里,意识到工作之外,只读过一本书。丹·布朗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。这就很严重了。
这本书最好的地方,在于他要你相信,好书已经足够好了,你要舍得辛苦。我也认同,阅读的一大销魂之处,是某个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好你的作家,在熬到百来页的时候,突然跟你勾肩搭背引为知己,不管你朝哪边看,都是四目相接;不管你怎么跑,都跟他踩在同一个步点上。
陈以侃在以一位真正的读者的身份,去创造一种作者文本,通过称叹、训斥与从不间断的调试,去接近那些难以言喻的瞬间,某个自我的核心。与此同时,他还拥有一副那么迷人的腔调:无比桀骜,又像在密谋。使人想要痛击,或者与之痛饮一场。——班宇,作家
陈以侃下笔有一种罕见的、时刻具有自觉意识的诚实——其实这很难,因为它一不小心就会被理解成自恋。读完这本书,在收获了无数让人为之击节抑或陷入沉思的见识之余,我也清晰地看到一个倔强的、试图从平稳持重中突围而出的写作者的轨迹。他熟读经典,却也质疑经典;他迷恋技术,却也解构技术——他永远更敏感于捕捉浩瀚文本里的那一点僭越的灵光。——黄昱宁,作家
我羡慕陈老师总是可以奋不顾身、毫无保留地投入他喜欢的作家和文本,也羡慕他转身又能找到描述和评价这种热爱的距离和准确性。他本质上和他写的那些有趣而有才能的灵魂是一类人。或者让我再诚实一点,这种羡慕其实已经严重到了嫉妒的程度。——吴琦,《单读》主编
任何编辑能够拥有陈以侃这样的作者,都是一大幸事。对我来说,拿到他的稿件之后,除了必要的技术处理,几乎不用任何改动,剩下要做的,无非就是欣赏他炼字锻句的工夫与推敲琢磨的巧思。我觉得他的这本文集,除了提示作者可以怎样写之外,更大的作用还在于提示读者可以怎样读。所以,任何作者拥有陈以侃这样的读者,也是一大幸事。——郑诗亮,《上海书评》执行主编
你可真敢胡来,陈老师那是多厉害的人和书,要我多嘴。——苗炜,作家

赵桥村
作者: 顾湘你不断去想象一块土地应有的样子,久了,那应有的样子就加入了这块土地;你不断面对一块土地沉思,久了,精神中就有了这块土地的气息。顾湘的赵桥村,差不多可以看成现实的居住地与想象的家园的交织,因为写得从容舒展,读的人就有了在其间优游居停的欢喜。
——黄德海(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,第17届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文学评论家)
2014年,顾湘从上海市区搬到赵桥村,这里靠近长江入海口,面对崇明岛。仅仅二十公里的空间位置偏移,带来独特的心理感受。
仿佛置身RPG 电子游戏,在《赵桥村》中,顾湘在城市寓所和村子的不同地点间漫游,在村外的汽车海与垃圾高原中冒险。她观察到菱在河塘里以斐波那契螺旋线展开,还见证了一场巨大的台风。最终这一切汇成一个数字时代下季节与自然的故事,一曲21世纪都市与郊区日常的咏叹调。顾湘的散文与画作充满细节,仿佛宽银幕电影,放映着当代生活的残破与宇宙永恒的神圣。

诗人十四个
作者: 黄晓丹十四位古代诗人和一个现代闯入者
一场始于1600年前的诗歌沙龙
七堂围绕“春天”意象与“青春”经验的文学课,
以现代心理学解读古代诗人,
诗与心灵自由飞动,
抵达诗歌中那些恍兮惚兮的微妙细节,
让古代心灵中幽微隐秘的部分重见天日,
成为与现代生命体验共情的丰富资源。
《诗人十四个》围绕“春天”意象与“青春”经验,用古诗词阐释友情、孤独、情欲、死亡、别离五种生命事件,渴求与接纳两种生命态度。全书根据这些主题分为七章,每章选择两个诗人,讲解其在这一主题下的文学样貌与诗人个人气质,并在两个诗人的对比中,呈现诗歌的不同解读,展现生命的矛盾性和可能性。

寂静的孩子
作者: 袁凌《寂静的孩子》是作家袁凌历时四年走访、探察、记录、沉淀,全新写就的一部非虚构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,袁凌将他的目光聚焦到了孩童的身上,他关注当下中国城乡儿童的生存困境,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、日常劳作和精神状态,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,最终完成了这一份关于孩童的生活和人性记 录。
留守、随迁、失学、单亲、孤儿、大病……儿童在困顿与匮乏的境遇中艰难挣扎,却又顽强成长。儿童的生命本应该是奔流的瀑布,自由而快乐,但这些孩子的声音却受制于阶级、地缘、身份的壁垒而无法被传达。《寂静的孩子》就是关于这样一批儿童生存境况的详实记录。打破壁垒,克服距离,在我们的世界里,他们的声音不应如此安静。

我与父辈
作者: 阎连科《我与父辈》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,是阎连科对父辈的一次写作祭奠,是一个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、回想和懊忆。
“我不断地回家、回家、再回家,把写作《我与父辈》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,直到觉得自己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,才可以重新上路远行。”
◆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,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,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,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自己的身上,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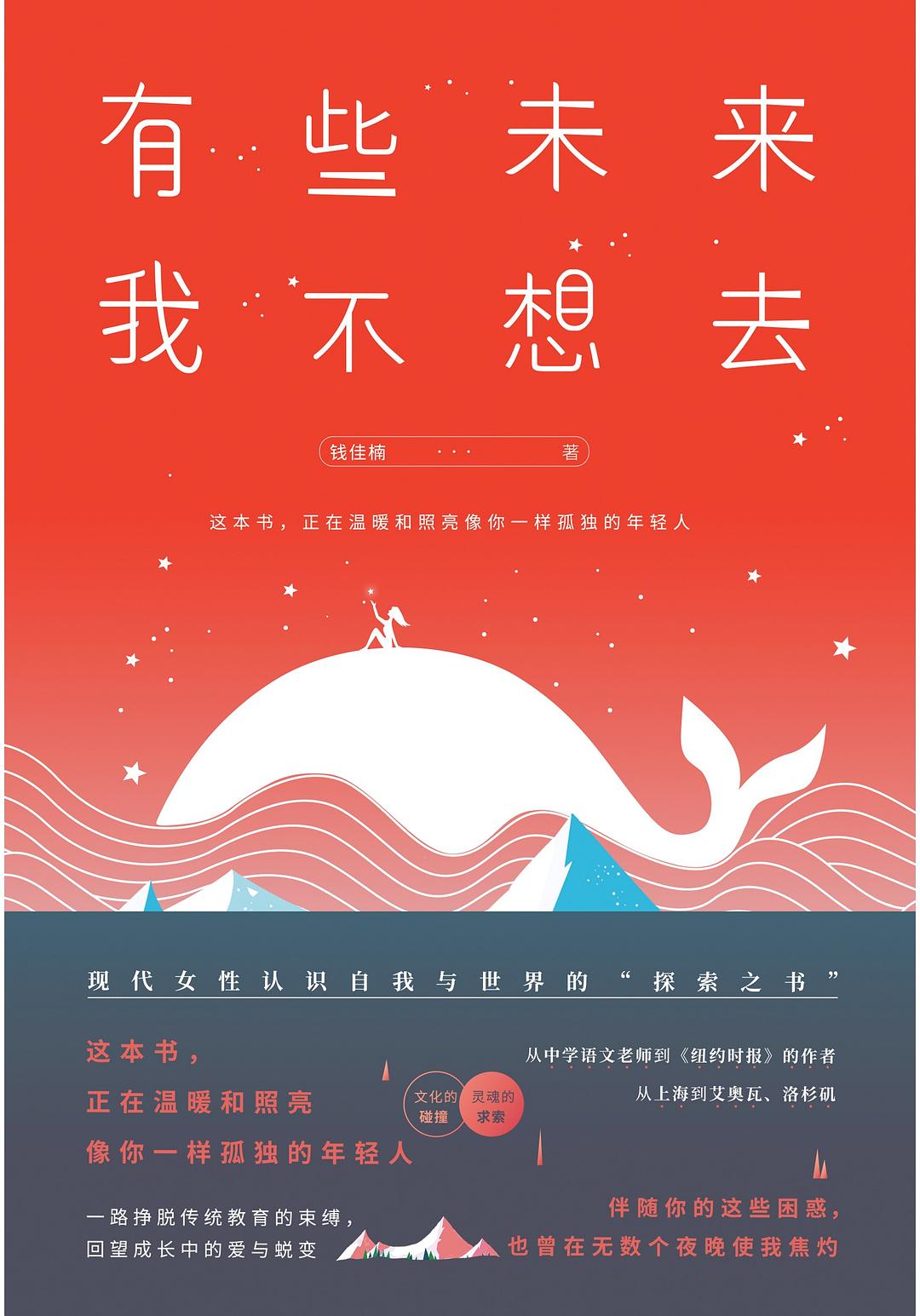
有些未来我不想去
作者: 钱佳楠 《有些未来我不想去》是一本书信形式的随笔集,每一篇都是写给“亲爱的人”,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渴望有这样一个倾听者,这29封信也是作者写给每个阅读此书的陌生人以及自己的。内容包括成长的追问,对多元文化的理解,梦想的坚持,关于爱情的困惑……每一篇都饱含了作者的深情和对人生的感悟。这些文字或许是黑夜里一闪而过的星光,虽然转瞬即逝,但也足以支持我们抵达下一个光明的时刻。
谈话录
作者: 王安忆 / 张新颖◆七次旗鼓相当的谈话,呈现文学创作的纯粹之美
作为中国当代重量级作家,王安忆身上同时有历史的厚重和时间的革新,她的作品既切中了时代痛点,又和速朽的潮流保持着距离。而作为兼具学识和才情的批评家,张新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现当代文学,用力透纸背的书写刻画着作者与时代的关系。阅读本书,即是欣赏两位势均力敌的谈话者在美学和智识上的碰撞。
◆几十载笔耕不辍,以工匠精神凿开文字与心灵的通道
王安忆认为:“文学是需要终身学习、认识、实践的过程,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。”她将文学融入生命之中:“文学家就是工匠,就是在做活,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……我们强调独创性,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,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。
◆以作家视角看同行,畅谈与汪曾祺、王蒙、莫言、余华、迟子建等人的交往经历
“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,写两类东西最好,一个是劳动,一个是享受。”
“王蒙是一个太聪明的人,真聪明啊,我觉得他真的是知道什么是好,什么是不好……”
“你看,莫言这么粗壮的一个汉子吧,忽然之间能写出这么灵巧的东西,真的就是神来之笔。”
“余华他会给你什么印象呢,他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。”
“迟子建的意境特别美好,这种美好,我就觉得是先天生成,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。”
本书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真诚对话,是一部个人写作史,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一次回顾。
在书中,王安忆谈到自己如何感受写作的快乐,坦承文学道路上的几次重大转折。她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观,谈小说家如何打量日常生活,谈虚构与审美化的力量,谈创作者对时代的关切和疏离。她回忆与冰心、宗璞、汪曾祺等文学前辈的交往,谈及陈映真、史铁生、陈丹青等对自己的影响,畅谈与莫言、余华、阿城等当代作家的相知相惜。

拔蒲歌
作者: 沈书枝《拔蒲歌》是一本“还顾望旧乡”之书,这“还顾”的内容既包含过去,也写及现今。开篇《儿童的游戏》,讲述儿时乡下常见的游戏。其后三辑:“红药无人摘”“瓜茄次第陈”“与君同拔蒲”,则别分书写乡下花草、南方吃食、少年心事及如今在城乡两地的生活。
在乡村日渐凋敝,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,作者用真诚质朴的文字,为读者记录下从过去到现在乡下的生活。她笔下的“南方”,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用来抵御外部庞杂世界的精神乡土。